策划:肖珊
撰文:余佳奥、吴茹梦
题图:袁昕语
采访协助:武祺迅、许童言、马宇欣、纠轲寒
出品:武汉大学大学生新闻社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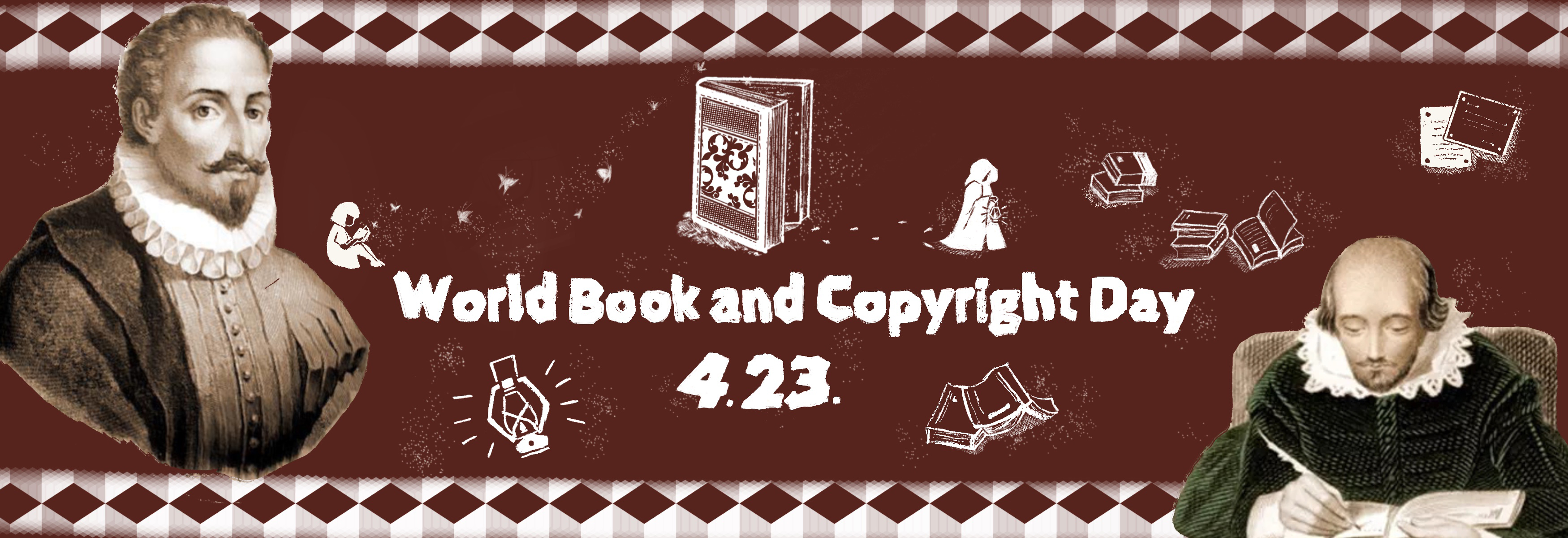
“可惜一切美好终将不再,
风刀霜剑或者繁花辞树。
而你的长夏之花永不枯萎。
……
只要人们能够呼吸,只要目光能够触及
这首诗就与你同在,在这世上流转不熄。”
一六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,一颗“能够了解地狱、天堂与人间”的伟大心灵就此搁笔。正如《十四行诗》中第十八篇所预见的,莎士比亚的灿烂长夏永未褪色。历史上的这一天,文学的天空注定明明灭灭: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于窘迫中带着他不朽的乐观病逝,纳博科夫在俄国圣彼得堡的显赫之家诞生……
作为读者的我们,难以企及作家们的瑰丽想象和魔法般的笔触,凭借白纸黑字便可创造一个至美的世界,常常自惭形秽。然而细想之,能与天地万物共情的写作者,他们祈盼的岂是“天上一轮才捧出,人间万姓仰头看”的殊荣?百年后的今天,如何让典籍册页发挥最大的价值?是什么让作品永葆永不枯竭的生命力?
“所期石炼能补天,但使珠圆月岂亏”。或许,每个人的能力与修为会有限定,我们能做到的,是保持敏感与思辨,发掘自己的潜质,如美玉晶莹,又如鲲鹏高远,成为一个合格乃至优异的读书人。
一场“经典”与“碎片”的二元思辨
在信息浩繁、资讯膨胀的时代,如何选择一本“好书”,是当下每位读书人或多或少面临过的难题。
所谓“好书”,很多人会下意识地将其诠释为经典之作,也即那些经久不衰,内容被大众普遍认同,或在某专业领域具有权威性与典范性的著作。
诺贝尔奖得主、南非作家库切总结说,那些“历经最糟糕的野蛮攻击而得以劫后余生的作品就是经典”。
“读经典就像是直取足金,读杂书就像是沙里淘金”,《大学图书馆学报》副主编、年近五旬的王波学长,回忆在武汉大学求学时的读书生活,常常遗憾读了太多杂志、期刊等,少读了经典和全集。
其实,早在十九世纪,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便对时下最畅销的流行读物保持着几分怀疑,告诫读者拿起经典:“对于善读书的人,决不滥读是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即使是时下享有盛名、大受欢迎的书,如一年内多次再版的政治宗教小册子、小说、诗歌等,也切勿贸然拿来就读……不如把宝贵的时间用来专心阅读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,这些书才真正使人开卷有益。”
除了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提取菁纯,经典阅读也是我们接引文明脉络、确认文化身份的自觉途径。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“如何度过大学四年”的演讲中谈到,所有的学生“必须打好自己专业基础知识的底子”,其中一个要点,即“读经典著作”,如中国古典的《论语》《庄子》《老子》《史记》,中国现代的鲁迅、周作人、胡适,外国的莎士比亚、托尔斯泰、歌德等人的作品。
来自不同年级、不同专业的学生,对经典有自己的感悟。弘毅学堂人文科学试验班的单新尧正在阅读《论语》,她说总有些经典中的经典,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拿出来阅读,因其具有超越时空的旷远和醇厚,可以相伴我们终生,值得反复精嚼细味。
文学院的曹家明认为阅历之浅深,与阅读所得之浅深不无关系。若用“看山”来比喻“看经典”,则有三个境界:看经典是经典、看经典不是经典、看经典还是经典;若用“赏月”来比喻,则从“隙中窥月”到“庭中望月”再到“台上玩月”。
由表及里,上述所言大抵是人们读经典时常需经历的三个阶段。可见,阅读经典既要从书中读出知识,又要结合对社会、人生和宇宙的认知,读出更重要的慧见和灵韵。
根据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,大学生正处于自我统一性与角色混乱和成年早期孤独感的阶段。在这样的人生阶段阅读经典,是十分合宜的。
真趣书社副社长、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的徐沁和朋友们,常在生活中体会青春的无常之感:对未来充满迷茫与不知所措,自发地思考生活与生命的意义栖于何处。阅读经典时,徐沁发现,文豪与先贤们也曾经历这样的时期,她的“无常与孤独”便不再那般强烈。
赫尔曼·黑塞的《德米安》、安德烈·纪德的《窄门》、路遥的《人生》等,讲的都是这个年龄段所面临的问题,书与现实相互映射、关照,给书外惶然的青年无穷启迪。
徐沁同时指出,“只读经典”对青年来说不太现实,毕竟理解力与鉴赏力有限,而且经典作品大多艰深古奥,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耐心去啃下一本大部头。
在真趣书社内部,社员们平时阅读的书目种类繁多,并不囿于经典或非经典,或是某一特定的种类。“读书是一件人性化的事情,用是否阅读经典来评判一个读者是不妥的,最重要的是书给你个人带来的触动。”
关于选书,不同的爱书人提出了诸多有趣的观点。对阅微书社社长、信息管理学院的邓宁馨来说,她喜欢在与书友的交流中找寻灵感。徐沁喜欢顺着自己喜欢的作家去发掘新书,在书中看到作者引用其他作家或书籍的观点,如果她感兴趣,也会找来读。水利水电学院的梅潇,会在bilibili上观看“学习UP主”的vlog,从他们的推荐书单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。在曹家明看来,“废话少、对胃口”就是好书。
尺素风雅,当如何赏之?
读书,并不要求总是正襟危坐。理想的读书境界,是青山与我两两相忘的浑然天成之境。置身周边的水声山色,书的诗情画意与人的喜怒忧乐如出一辙。恰当的景、情、人,对于从阅读中获取乐趣,大有裨益。
珞珈山四时分明,绵长的雨后清晨、樱花纷飞的午后、疏朗的中秋之夜……时令之变,牵动人的心绪随之变幻,在特定的情景下读特定的书,往往会加深对某一主题的感悟与理解。
譬如在七夕,读一读《我用爱意给孤独回信》《朱生豪情书全集》《湘行书简》《千曲川风情》,哑然于文人雅士的爱意绵长,与浪漫撞个满怀。在某种氛围感中阅读,是一种极美妙的生命体验——
从高中开始,邓宁馨便享受这种特别的“仪式感”了。她喜欢在开着樱花的墙角读书,坐在墙头,樱花落在书上,一朵、两朵……终至缤纷。人、书、花相映成趣,“那种感觉太美好了”。
“浅淡云卷,晴明松间,但乞雪皑皑,能留你在此。浅淡云卷,晴明松间,即使天无晴,山茶亦无情。”读《雪国》的时候,正在文学院读大三的颜雯迪“恰好”病着,川端康成的《雪国》处处弥漫着物哀的感情,因此她看《雪国》的眼中也时常晃着凉的泪,好像是雪国的雪和绉衣也哀哀凄凄地盈盈飘过榻前,不化不散。
阅微书社曾举办一场科幻文学读书会。是夜,在万林艺术博物馆的天台上,没有掌灯,只燃着几粒烛火。恰逢星月皎洁、明河在天,在珞珈山的星空下谈论科幻文学,思想的锋芒融聚、炸裂,照亮了身处其间的读者。
爱书人往往有自己的阅读程式。单新尧喜欢在下雨天泡一杯茶,放上轻音乐,进行无人打扰的阅读,翻看的多是泰戈尔的诗选。
对曹家明来说,氛围感可以去寻找,但不宜刻意营造。雨天、落地窗、红茶;东湖、鸭禽群、阳光;爵士、鸡尾酒、小夜灯……意境到了,拿起一本书来读便好了,诗意在眼前、更在心间。“随意一些,是品书,也是品生活。”
晚明文人吴从先在《赏心乐事》中曾直抒自己的读书之见:读史宜映雪,以莹玄鉴;读子宜伴月,以寄远神;读《山海经》、《水经》、丛书、小史,宜倚疏花瘦竹、冷石寒苔,以收无垠之游而约缥缈之论;读忠烈传宜吹笙鼓瑟以扬芳;读奸佞论宜击剑捉酒以销愤;读《骚》宜空山悲号,可以惊壑;读赋宜纵水狂呼,可以旋风;读诗词宜歌童按拍;读神鬼杂灵宜烧烛破幽……可见读书之法千千万,氛围一事,不过一隅。
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张琦喜欢先看封面、封底,再看内容,引言结语也都不会跳过。看到绝妙处,十分欣喜,会再看一遍。
弘毅学堂的王思源在阅读时喜欢涂涂画画。学术方面的书,如果他认为这段文字对未来的学术写作有所助益,会随手复制到自己的笔记中,标明出处、整理归纳。
英国作家伍尔芙曾对读者给出建议,“对于读书,一个人能够给别人的唯一忠告就是:根据你的见解,运用你的理智去获得自己的结论,不必接受别人的观点。”
无独有偶,做到“不带偏见的阅读”,也是纳博科夫对读者的要求,“要有不掺杂个人情感的想象力和审美情趣”。除破除前见、运用理性之外,纳博科夫期望优秀的读者同时兼具灵感、激情和想象力。
而读书交流类社团的存在,则向我们展示了集体阅读的魅力与价值。
每逢冬至前后,真趣书社都会举办一场围炉诗会,有诗有茶,是新式的“红泥火炉”和“绿蚁新醅”。一群人围坐,诵诗、谈天、分享感受,倾吐自己的、倾听别人的。
相比于私密的个人阅读,集体阅读要求更多观点的表达。要表达,就要“反刍”,把脑海中庞杂的思绪与思考条理化,有意识地进行设计与加工。有表达,就有共识与异见,在交流中经由别人的思绪和观感收获一些额外的触动,发现了一些新奇的角度。这些是集体阅读的独特乐趣。
如珞珈,也如鲲鹏,见自己,也见众生
书,宛如一面圆整的平湖之镜,行人驻足岸边,可清楚照见其心灵的深与广、乐与忧。想要成为一名优异的鉴赏者,当于读书间认识自我,检省自我,不断提升人文素养中的感性思维与灵性思维。
虽是寂寞之道,要做到却并不困难。作家张晓风在《前身》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阅读观与生命观,“当我们读一切历史,一切故事,一切诗歌的时候,我们血脉贲张,我们扼腕振臂,我们凄然泪下,我们或哂或笑,或歌或哭,当此之际,我们所看到的岂是别人的故事,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自己。”
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,我们有时正是那等待知音者驻足听琴的伯牙,是渴望回到旧日茅舍去的陶潜,是辙环天下踯躅津口困于陈蔡的孔丘,也是登高望远,赋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,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”的陈子昂。
我们又何尝不是赍志以殁的诸葛武侯,是众人笑叱声中破盔疲马走天涯的唐·吉诃德,是海明威笔下,墨西哥湾流中,那个出海三日,筋脱皮绽却只拖回一副比渔船还长的大鱼骨架而回航的老渔夫……
读书,让我们在一切往者身上看到自己,仿佛活了千千万万遍,经历了累世累劫。
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翻译系毕业生李晨若,曾做过一期《充满奇想的一年》的真人图书推介。在推荐语中,她写道:“在《充满奇想的一年》里,美国女作家琼·狄迪恩抒写了丈夫去世、爱女重病一年间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思、所想。四十年共同生活的片段与回忆,细腻而又充满温情……人类只是时间的客人,在回忆中,她看见了人与疾病抗争、与命运抗争的全部力量。在看似平静的叙述中,我们与作者一同体会着猝不及防的生离死别。”
恰恰如同这滞重而悲痛的荐语,书的动人,在对人性的关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“人”不仅仅是书的阅读者,更是书中永恒的主人公。
颜雯迪认为,读书也是一种陷阱,读者往往需要走进先贤的情感里。若读者的灵魂不稳,则易于迷失;若灵魂贫瘠,将与一切无缘。因为“窗口决定让多少月光探入屋子里”,当你不再拥有墙,你才会拥有整只月亮。
一首《枫桥夜泊》,众人多是读见残酷现实里孤寂的夜,霜冷星寒,枫桥“渔火”的爝焰绝美,更显落第之人的悲哀。张晓风却并未感到惋惜,而是读出了另一种心情,“有人会记得那一届状元披红游街的盛景吗?我们只记得秋夜的客船上那个失意的人。”因此要感谢上苍,“如果没有落第的张继,诗的历史上便少了一首好诗,我们的某一种心情,就没有人来为我们一语道破。”
向内探求己心,在他者身上看到无数自己的影子,可以开拓心灵,将心思锤炼得幽微而聪颖。与此同时,书也指引我们对个人不断做出判断和调整,进行综合提升。
在曹家明的眼中,书不是镜子,而是钉子,是人进行自我雕琢的中介。人可以通过书发现自我塑造的契机和途径,但书不会自发地塑造人。这一点,和我们传统印象中的教育别无二致。
弘毅学堂理科试验班的张骞月正在重读毛姆的《月亮与六便士》。梦想与现实的冲突,带给了她无尽的思考。张骞月在阅读中,不断探索着自己人生的“平衡之道”。
书赐予读者人格之美,也赋予人们胸怀和由内而外的精神力量,而读者的存在,亦使书的意义得到了更好的实现。
徐沁认为,读者群体的存在,让书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,而不至湮灭。读者的正反馈会给作者信心,并诞生更好的作品,同时吸引更多的人来阅读;对于书籍的评价,也大多由读者定夺。书的价值在这些层面得到实现。
在邓宁馨眼中,身处当下的网络语境下,读者对书籍的二次创作,如书评、小说的同人作品等,在另一个维度扩大了书籍的影响力,挖掘了书籍的深意。
书与人,相互关照,也相互成就。借用诗人鲁米的抒情诗来作结,“黑夜离去,我们的故事讲不完”。书籍与读书人协作共奏的文化交响曲,将在历史的长河中声声不息、世代回响。
武大学子当如珞珈,也如鲲鹏,应当坚韧如磐石,晶莹如美玉,也应当高瞻远瞩,志存深远如鲲鹏,有着博大和超旷的情怀。武大校园里喜好阅读、正在阅读的人们,同时也将视野放到了他者和远方,关心着更广阔的世界与更遥远的未来。

(稿件来源:《武汉大学报》1554期3版 编辑:肖珊)